目录
快速导航-
小说视界 | 奋斗的青春
小说视界 | 奋斗的青春
-
小说视界 | 安喜门
小说视界 | 安喜门
-
小说视界 | 不差钱
小说视界 | 不差钱
-
散文短章 | 南阳三章
散文短章 | 南阳三章
-
散文短章 | 草木知心(五题)
散文短章 | 草木知心(五题)
-
散文短章 | 春入馔
散文短章 | 春入馔
-
散文短章 | 墨香盈满读书台
散文短章 | 墨香盈满读书台
-
散文短章 | 山阴春韵
散文短章 | 山阴春韵
-
散文短章 | 陌上野菜莼鲈思
散文短章 | 陌上野菜莼鲈思
-
散文短章 | 回不去的故乡
散文短章 | 回不去的故乡
-
散文短章 | 母亲和她的羊们
散文短章 | 母亲和她的羊们
-
散文短章 | 炉边往事
散文短章 | 炉边往事
-
散文短章 | 桐花入梦
散文短章 | 桐花入梦
-
诗歌前沿 | 故乡的原风景(组诗)
诗歌前沿 | 故乡的原风景(组诗)
-
诗歌前沿 | 日常之诗
诗歌前沿 | 日常之诗
-
诗歌前沿 | 薛省堂的诗
诗歌前沿 | 薛省堂的诗
-
诗歌前沿 | 望乡(组诗)
诗歌前沿 | 望乡(组诗)
-
诗歌前沿 | 无尽(组诗)
诗歌前沿 | 无尽(组诗)
-
诗歌前沿 | 聋子伯
诗歌前沿 | 聋子伯
-
诗歌前沿 | 眷念三题
诗歌前沿 | 眷念三题
-
诗歌前沿 | 大风吹(外二首)
诗歌前沿 | 大风吹(外二首)
-
南阳青年作家专栏 | 新野二记
南阳青年作家专栏 | 新野二记
-
南阳青年作家专栏 | 青青菜园
南阳青年作家专栏 | 青青菜园
-
南阳青年作家专栏 | 猴戏
南阳青年作家专栏 | 猴戏
-
躬耕论语 | 亲密性,以及情感对观念的转化
躬耕论语 | 亲密性,以及情感对观念的转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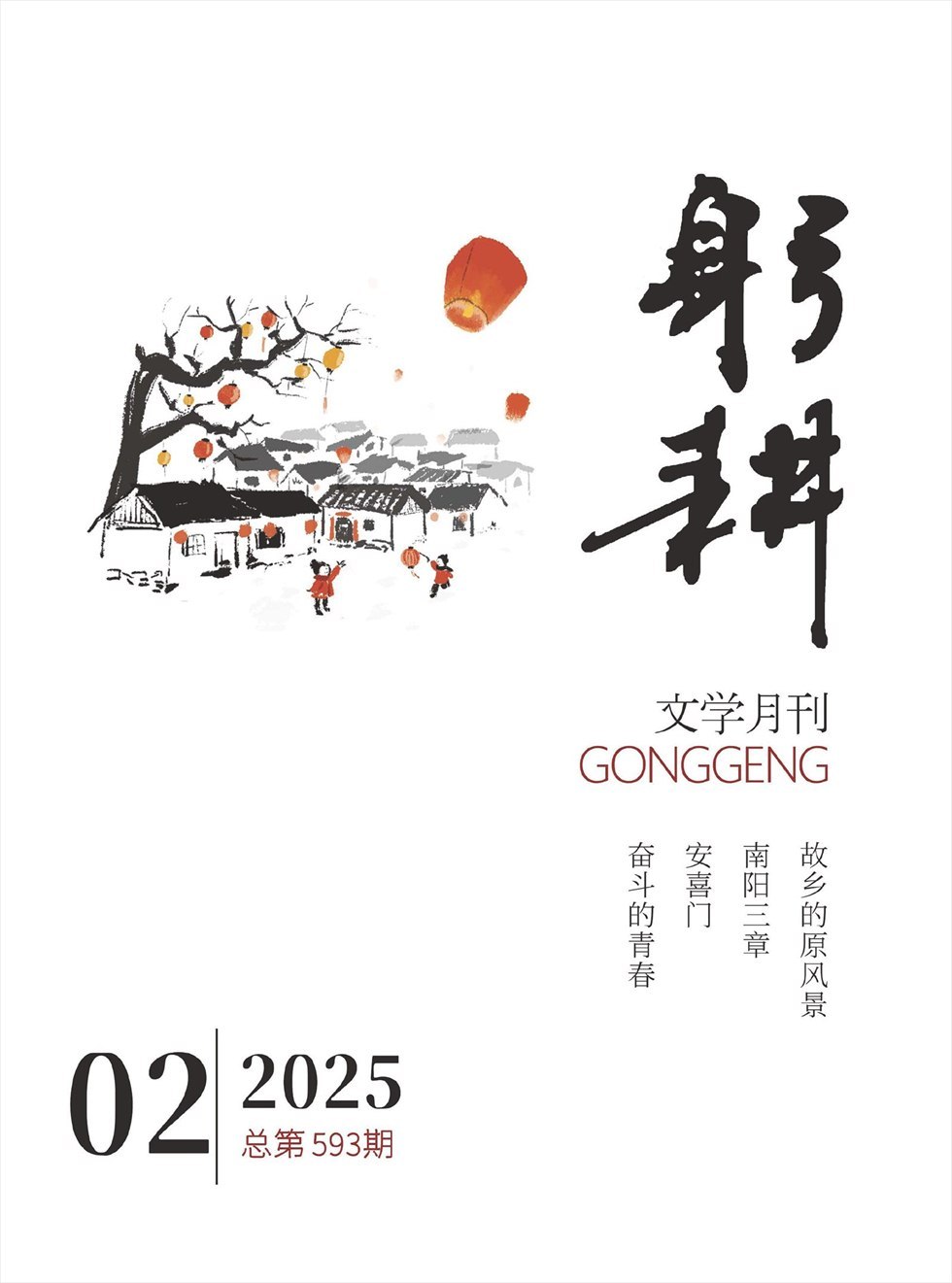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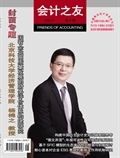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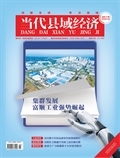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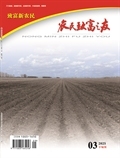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